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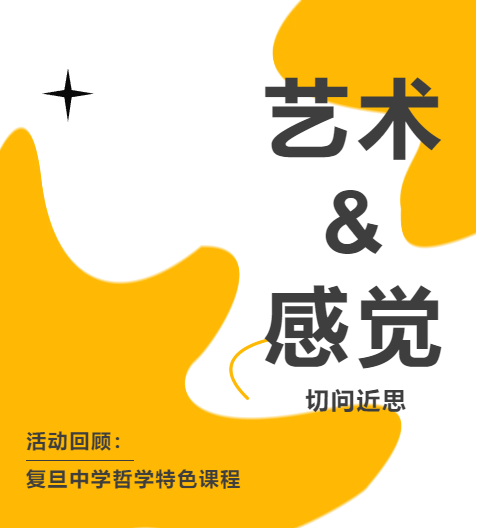
怎麽證明這次的我還是上次的我☆?
在9月27日的課堂伊始,孫老師首先拋出了一個問題:“怎麽證明這次的我還是上次的我?”由此🔜,展開了對於上一節課內容的回顧:在上一節課中提到,為什麽在教堂的雕塑與畫作面前,有些識字的人也會駐足停留👃🏽?與那些不識字的人的目的不同,他們已經了解這些故事👩🏽✈️,那麽為什麽他們還會站在藝術品前停留呢?

審美意義的綻出
接著🌏,孫老師以《小王子》中狐狸和小王子的故事為例開始講解。他引用了《小王子》中的一段原文🆚🎛:
“我的生活很單調。我捕捉雞,而人又捕捉我。所有的雞全都一樣,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樣。因此,我感到有些厭煩了。但是🚶♀️,你要是馴服了我♞,我的生活就一定會是歡快的🪲。我會辨認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腳步聲🧖🏼♂️。其他的腳步聲會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腳步聲就會象音樂一樣讓我從洞裏走出來。再說,你看!你看到那邊的麥田沒有?我不吃面包💂♂️,麥子對我來說,一點用也沒有。我對麥田無動於衷。而這,真使人掃興。但是,你有著金黃色的頭發。那麽,一旦你馴服了我,這就會十分美妙。麥子,是金黃色的✧,它就會使我想起你。而且,我甚至會喜歡那風吹麥浪的聲音……”
孫老師說👨🏻🚀,狐狸的這番話告訴我們🗂,原來它也曾看到過雞和人,也曾感受過風吹麥浪,也曾看到過麥子金黃,但那個時候每一只雞,每一個人對它來都是一樣的🧙♀️,即😐,任何一只雞都可以是它的捕捉對象,而任何一個人都是它要躲避的對象。它對這些東西的感覺是單調的🧑🏿🦲,其中沒有什麽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但是,在小王子馴服了狐狸後,狐狸就從這樣單調的尋常關系中解放出來👸🏼,它會有視覺和聽覺的變化,它看到麥子的金黃色,就會想起有著金黃色頭發的小王子🏌🏿♀️,這個感覺非常美妙🎄🏃🏻♀️➡️;這樣的視覺和聽覺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新的感覺,這種感覺讓它喜歡上了風吹麥浪的聲音……這樣的感覺有著審美的意味🦮。

對於這一點🥰🏌🏼♀️,孫老師聯系杜威《哲學的改造》中的一段話給出了進一步的說明,杜威在書中寫道👱🏽♂️,“一朵雲有時暗示一匹駱駝🧜🏻♂️,有時暗示一個人的面孔。這些暗示,若非曾經見過實際的真正的駱駝和面孔9️⃣,就不會產生𓀜。但實際是否相似卻沒有什麽關系,根本要點是在那追蹤旋生旋滅的駱駝或面孔的行跡時的那種情緒的興趣。”孫老師說:被馴服後的狐狸之所以能夠在看麥子的金黃時想起小王子金黃的頭發📸,麥子和頭發這些本來無關的東西之所以變得有關起來,乃是因為emotional interest(情緒的興趣)。Interest可以拆解來看:inter表示彼此間的🙂↔️、相互的,而est則是法語中的系動詞變位。而對於人來說,要是我們被想象力所馴服🏄🏽,那麽所有的一切,都會變得奇妙而不同尋常,我們也會因此而擁有審美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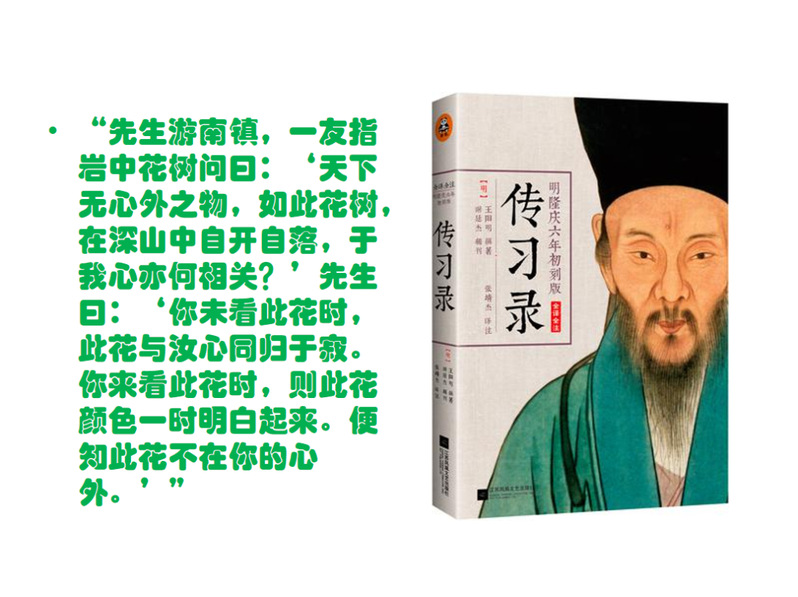
王陽明曾說“天下無心外之物”,這是因為萬物都會與人心發生感通的關系。就像月亮,如果月亮對於人類而言只是距地球38.4萬千米外的一顆天體🧚🏼,那麽又怎麽會有李白在“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中寄托在月亮上的無限情思?感通一詞源於《周易·系辭上》。

接著👩🏽🔬,孫老師又為同學們帶來另一個例子:《莊子》中的“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在這篇文章中,莊子認為魚是快樂的💫,而惠子認為只有魚知道自己是否快樂。莊子之所以能感覺到魚的快樂是因為🍜,他與魚感通了🔕,他與魚發生了emotional interest意義上的感通;這種由感通而來的對魚的快樂的感覺,完全不同於將魚兒帶進實驗室,通過觀察神經變化所得知的魚兒的快樂😋。
感無通有
老師又為同學們給出了對於感通的進一步說明:感無通有。這就是,所感的東西是無緣無故、不可名狀的,是沒有明確的目的和對象的✹,但是,這樣的對於無的感又會通向作為“image”的有。為此,老師引入了《紅樓夢》的例子。《紅樓夢》裏的一首《西江月》中說寶玉“無故尋愁覓恨”🧑🏻🦳。這裏的“無故”就是指無緣無故、不可名狀的,就是對無的感。賈寶玉的愁和恨之所以無故,乃是因為他所愁的和恨的不是可以指認的東西,而是不可指認的生活本身🛀🏽。為什麽生活本身不可指認?因為只有活著的人🧡,才有可能問生活是什麽這個問題;可是🌺,活著的人已經在生活之中,因而無法把自己從生活中剝離出來以便把生活當作自己的提問對象⛑️。所以,“生活是什麽”這個問題沒有答案,這個問題只是激發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活出來。感無,就是感到這個作為無的沒有答案的問題的這種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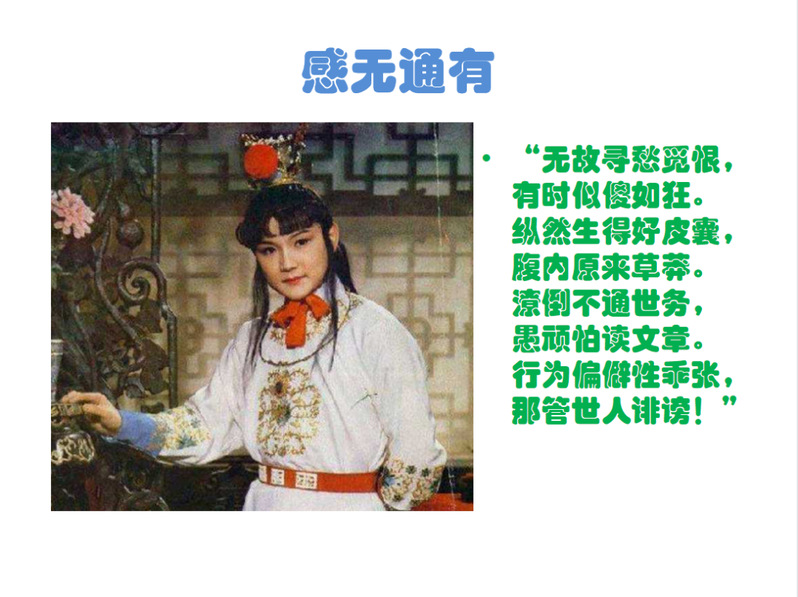
最後🧜🏻,老師告訴大家👱🏻♂️,生命的活動其實就是創造的活動,每個人都有一雙看得見美的眼睛,高中生正處在青春的最好年華,這是最富生機與活力的年紀🙆🏽♂️💇🏼♀️,這是最美的年紀,同學們應當以夢為馬👱🏿♂️,不負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