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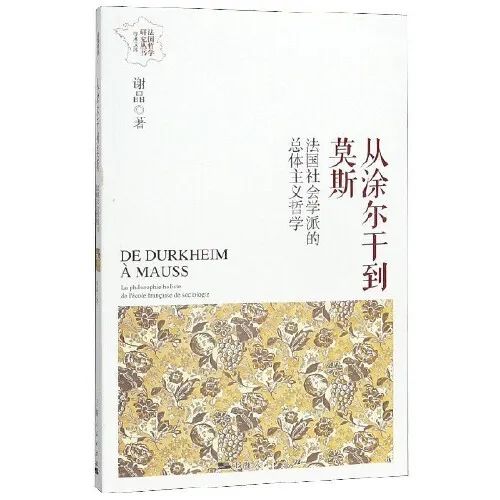
書本信息
作者:謝晶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9730
出版年月:2019年9月
開本:16開
內容簡介
以塗爾幹與莫斯為代表的法國社會學派為我們貢獻了經典的社會理論著作。《社會分工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論禮物》等作品皆在社會學與人類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較之於法國社會學派理論在社會學與人類研究中引起的廣泛討論,其哲學內核卻鮮有問津✮。
本書采用社會哲學的視角,旨在證明法國社會學派具有堅實的哲學內核👨🦯,並呈現這一內核漸漸完善自身的過程🦸♀️:從塗爾幹到莫斯📜,一種總體主義的立場漸漸擺脫了有機主義與實體主義的束縛,並最終實現了向著結構本體論的轉型🧑🏻🦯➡️👩👩👧。通過細究這一轉型,本書不僅希望澄清“社會總體”這一復雜概念,而且也希望呈現法國社會學的批判維度👰:“總體”不僅是塗爾幹與莫斯用來反駁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理論工具🔂,更是他們用來分析現代性並指出其弊病的策略。
作者簡介

謝晶,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利徐學社研究員✋🏽,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合作研究員,曾留學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師從VincentDescombes, ClaudeImbert, BrunoKarsenti等法國哲學家研究現當代社會哲學,曾擔任法國高中畢業班哲學教師🥷🏽🟡。主要研究領域有:現當代社會哲學,社會科學的哲學🔔,結構人類學🔺,法國20世紀哲學。譯有《話語,圖形》等🚵🏻♀️。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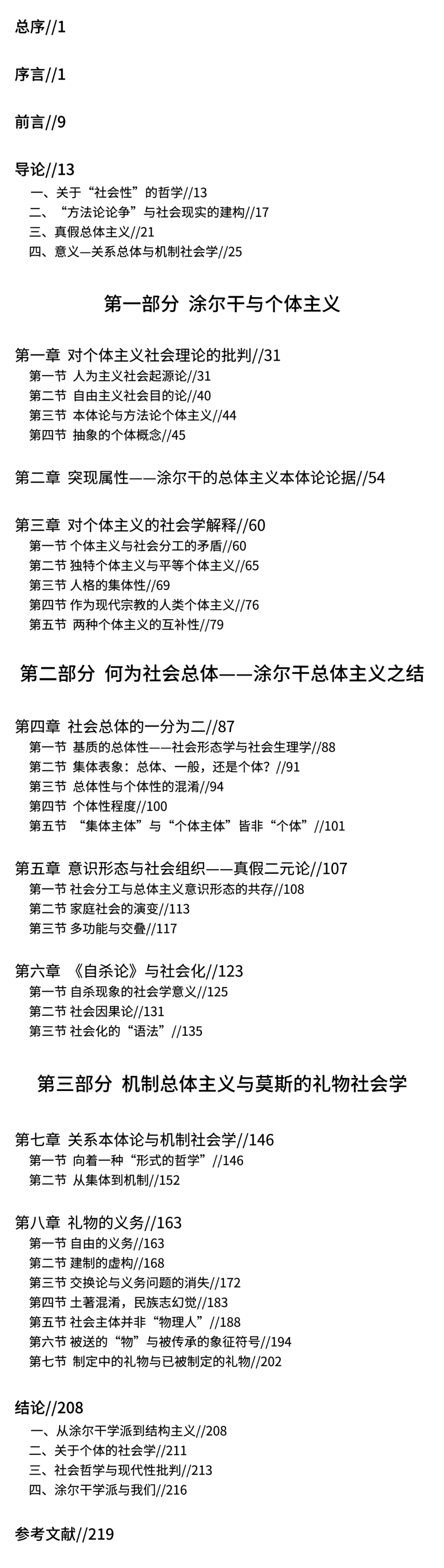
樊尚•德貢布序言(節選)
在人文社會科學傾向於以越來越專業和割裂的方式展開研究的今天🚣🏻,要承認某個社會學派——塗爾幹的學派——同時也是一個哲學流派🧓🏿,這並不是一件不可言喻的事👨💼。本書作者所從事的研究的價值,在於它呈現出了被我們匯聚於同一個思想傳統——法國社會學派這一傳統——中的那些學者所共有的社會哲學,尤其是這一哲學的內在一致性📘,它在不同作品中所相繼獲得的闡述之間的邏輯關聯。
由此,本書作者揭示出了在我看來20世紀法國哲學中最具創造力和前景的那個思潮的內在統一。
前言(節選)
本書的題目很可能令讀者以為這是一部思想史著作,事實上它屬於哲學研究,它自始至終圍繞一個問題展開:何種“總體”概念能用來界定社會現實⚉。如果說他以塗爾幹和莫斯的思想為線索,這是因為“社會總體”概念不僅直接構成他們的理論核心👩🏻🌾,而且從前者到後者經歷了一個發展乃至更新的過程😆。誠然🎆,在“追溯某個特定概念之發展”的意義上👂,本書的內容可以說涉及思想史。但即使是這種狹義的的概念史研究也非本書的最終目的🧑🎓。與其說筆者希望厘清塗爾幹與莫斯的思想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毋寧說筆者希望借此展開哲學論證↗️🌁。換言之,塗爾幹與莫斯並不是本書的考察“對象🦥,而是它的思考“土壤”🫧。
習慣於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史作品的讀者因而有可能對本書的行文感到不適乃至失望——他們在其中並不能找到系統和歷史性的介紹。筆者無意對主要作者的創作背景、思想發展和影響力等做系統的梳理,也無意對他們的作品作分門別類的綜述。作為本書“土壤”的概念史所內含的是另一種順序——“社會總體”概念從模糊到明晰,從矛盾到自洽的順序🕵️。
如果說任何學術作品都必然對讀者有所“選擇”,那麽筆者預設本書的讀者較之“事實”(包括思想事實)的堆積所更感興趣的是論證的推進。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必須對相關的“事實”(塗爾幹、莫斯、杜蒙🧑🏽🦲、列維-斯特勞斯等的作品和思想)已然有所掌握,也不意味著他們必須對社會哲學的問題已然有所涉足👩🏻🦯。本書的導論旨在向未接觸過社會哲學的讀者交代其問題意識⛺️🧖🏽♂️。至於思想史方面,倘若拙作能激發讀者對法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傳統的好奇👡,這方面的資料早已汗牛充棟,大部分原著也已被譯為漢語🦡。
出於同樣的原因🧝🏼,本書並不作“原著”和“二手材料”的區分——這是它或許會引起讀者不適的又一個原因。更確切地說,筆者所關註的都是“一手材料”。嚴格意義上的“二手材料”🧑🏽🚒,亦即處於社會哲學與法國社會人類學傳統之外,僅僅對之進行“客觀”解釋和評析🤨,或是立足於其它思想傳統而對之進行引介、評論乃至批判的作品,皆不在筆者的考察範圍內🧂。杜蒙、列維-施特勞斯、德貢布🤶🏿、卡爾桑蒂的名字之所以反復出現於本書中,仍然是出於“概念史”的考慮🏥。他們對於塗爾幹學派的評述皆是為了發展總體主義社會哲學,此為筆者的考慮之一。而他們自己的社會哲學又反過來澄清塗爾幹學派的社會哲學,此為筆者的考慮之二。例如,杜蒙對於兩種“個體”概念的區分所澄清的是塗爾幹所開創的關於“個體”的社會學視野;德貢布對於“集體個體”的批判所澄清的則是有機——實體總體主義的不足🧑🏻🦼➡️。正如德貢布在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所稱,“從塗爾幹到我們”存在著繼承關系。筆者希望通過在這些作者(德貢布所稱的“我們”)與塗爾幹及莫斯之間建立“內部對話”而探究何為“社會總體”。這種“內部對話”有時會涉及看似沒有任何交集的作者(例如本書第三部分所論及的梅洛-龐蒂的“形式哲學”),這實為概念史上常見的現象。
再一次,如實地反映塗爾幹和莫斯的思想,或如實地反映其影響,皆非本書的目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筆者允許自己對之作不如實的反映)。筆者的意圖與其說是用杜蒙🟡、列維-斯特勞斯😖、德貢布👱🏿、卡爾桑蒂等來註塗爾幹和莫斯,毋寧說是用他們所註的塗爾幹和莫斯來註一個當代的話題:總體主義社會哲學是否可取🧘🏿♂️。讀者很快就會發現,筆者希望為之作出辯護。所有對塗爾幹和莫斯理論的分析👱🏽♀️,所有對“內部對話”的重構🦙,這些看似屬於思想史的工作都並非“就事論事”,而是旨在獲得一種值得被辯護的社會總體概念。
結論(節選)
一、從塗爾幹學派到結構主義🧗🏼♀️:莫斯的結構主義思想是對塗爾幹總體主義的完成⛹️♂️⚅。列維-施特勞斯的“正史”構成雙重誤導。
二、關於個體的社會學:社會總體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對於“個體”的社會學定義。決定我們采取總體主義或個體主義立場的並不是我們考察的社會存在類型或層面😱,而是我們對於社會存在所采取的考察方式。
三🙋🏽♀️、社會哲學與現代性批判😬:從塗爾幹學派自始至終對“個體”問題所抱有的特殊關懷可以看出🥎,其立足點並非某種中立的科學立場(盡管其社會科學及社會人類學規劃很容易令人持此觀點),而是對於特定意義上或者說作為特定社會歷史現實的“現代”社會的反思。對於“總體”概念本身的不斷建構和改造,同時也是這一反思從溫和趨向激進的過程。
四📫、塗爾幹學派和我們🤾🏻♂️:如果我們認定我們也處於現代化進程中(這種認定本身已經是述行式)🫲🏻👩🦼➡️,那麽我們在如下意義上需要社會學:我們需要通過社會史追溯和徹底比較的方式,將一種意義關系總體特殊化和問題化為“我們”。將任何社會“理論”中的範疇或論斷直接運用於我們的做法都不是純粹的分析,而已經是對於社會現實的盲目建構——將他者的實踐“據為己有”,將他們的“我們”變成我們的“我們”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