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頻《郁喆雋🦸🏿:被祛魅的祛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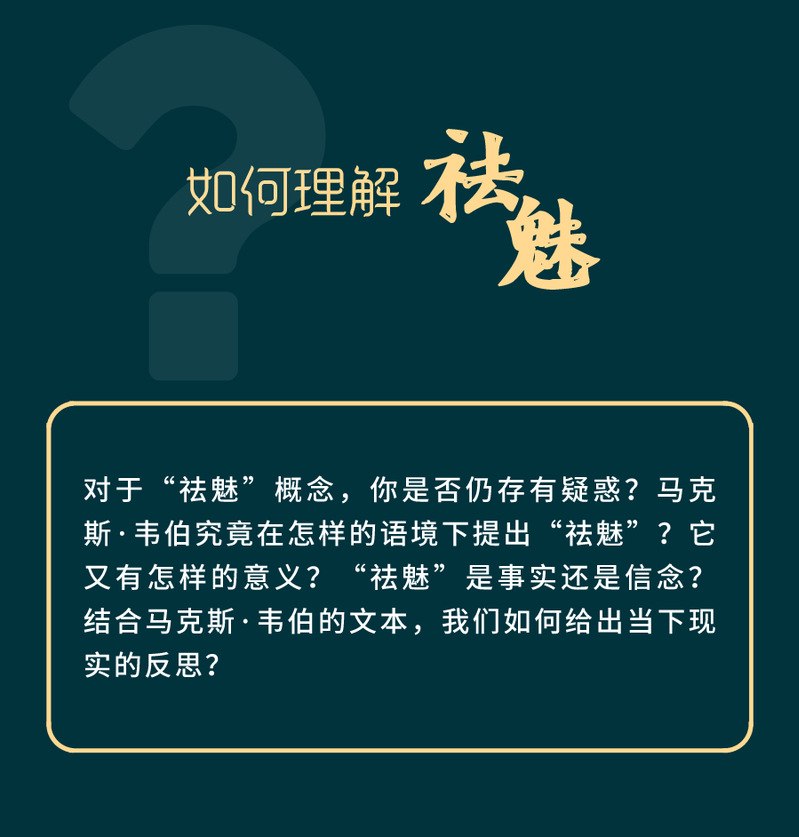
如何理解“魅力”?
狹義上,“祛魅”特別針對於宗教學或者宗教史當中發生的一個“轉換”。歐洲16世紀宗教改革後誕生新教,新教的儀式相比天主教簡化得多,其中尤為體現在聖餐禮儀中💇🏼。新教中💅👀,這一儀式和其相關的神學闡釋都發生了改變。此外👩👩👧,天主教歷史上的聖母崇拜、聖人崇拜等等觀念,在新教中不再存在。宗教史上的這一轉變於是魅”®️?成為專門研究的一個話題,後來韋伯將之闡釋為“祛魅”(Entzauberung)。就其本身含義來說👨🏼🎨,“祛魅”是指去掉一個儀式過程當中的巫術(魔法)成分。
進一步,從廣義的層面來看,韋伯將“祛魅”普遍化🥶,他認為這一去除巫魅的過程不僅是發生在狹義的宗教史上或者宗教儀式上的、神學上的變化🤜🏼,而且是貫穿在整個人類現代化進程當中的。韋伯的“祛魅”和其理論中的另一個概念——“合理化”是一體兩面的🕺🏿。只有把現實當中的一些“巫魅”、有巫術痕跡的東西去掉之後💁,我們的生活才會變得更為合理化,換言之,去除巫魅是我們進行合理化的前提。
在視頻中我有引用韋伯關於“去除巫魅”的一段話,它出自於韋伯的演講——《以學術為業》📨。這個演講的“密度”是相當高的🧖🏽♀️,其中它用了三個排比句闡明祛魅的意義。第一層是認知意義上的,即這個世界不存在神秘不可知的理由💄。以前我們會相信有一些神神秘秘的力量在起作用,不管是神明、鬼怪、精靈,還是有靈論,這種力量超出人的認知和掌握🦒。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如此這般的“力量”,比如“氣”,它很難為人的意誌所操控😊。“祛魅”的第一層意義就是認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沒有神秘不可測的力量操控的,是認知意義上的可認識的,而且它是具有規律的,甚至可以使用數學、邏輯或是日常語言進行表達的。以上便是祛魅的第一層意義表述,即認知上的無障礙🧖🏿。
“祛魅”的第二層意義從認識模式轉換到了行動者🕺🏻🍄、幹預者的模式,即在原則上可以支配——這是一個巨大的跨越,它與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有著直接關系。我們抱有一種信念,盡管現在還有我們無法掌握的東西,但經過技術的發展👩🦯,假以時日我們終究可以將其掌控🐀。這種信念導致現代人擁有一種盲目的樂觀,而這種樂觀還與另一個社會學進展有關——歐洲現代進程中的體製性分化。在分化前,原本歐洲在中世紀擁有強大的天主教權威,這種宗教力量足以將其他社會領域捆綁在它周圍,使得每個領域都並無獨立原則,宗教成為裁判的標準、最高的法官。但現代化開始後,每個領域都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比如經濟領域🤷🏿♂️,原本經商獲利過多被天主教認為是惡🚖,基督徒在中世紀被禁止放貸🧏🏿,但現代社會的每個領域,都有“在商言商”的現象🏌🏼,並拒絕進行一種泛道德化的評價,各個領域都獲得了獨立自主性🛴。而對於我們個人而言,我們在選擇職業時,每個職業都有自己內在的規律和價值🧏🏻♂️,比如警察🍐、法官、律師以維護社會秩序為業;老師以傳道授業為業🧓🏿;醫生以治病救人為業……
但隨著體製性分化的不斷增強,在宏觀上👹,某些領域會出現失控,即失去價值的引導,正如資本主義中經濟力量過強會成為一種非人的力量,政治如果不講道德會失去最終目標等等;而微觀上,對個人而言,“祛魅”使得我們在生活中產生“群體性的幻象”。我們更傾向於直接相信“專家”,因為我們認定專家與非專家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作為人的我們不可能掌握所有領域的知識。例如我買了一個手機,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但這不妨礙我的使用,而且我相信總有一些專家會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如此就變成了我們對專家的一種盲目信任。我們個體解決不了的問題,我們相信人類這個群體是可以解決的,這和“祛魅”所造成的盲目樂觀又重疊在一起,變成了一種人空前的自信——即便個人不知道,我也相信群體可以解決問題。
例如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很多人處於盲目樂觀中,認為社會上的醫療專家等力量一定會迅速解決這一問題,但其實是可能過大過高地估計了我們人類整體的力量。而且在當下的媒體的環境中🧚🏼♀️,這種“盲目樂觀”造成的結果是普通人有這樣一個預期🦶🏻:我回答不出來👨🏭,專家可以回答出來。但實際情況如何呢?有時最前沿的科學家會告訴你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這是非常真誠的一個回答。只能說研究越多,越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者說“存有爭議”、“沒有定論”。但這種回答顯然不討好,因為大眾希望專家繼續扮演一個“先知”或者“半神”的角色,必須要給出答案。不然怎麽叫“專家”呢?專家的“人設”就是必須給出答案🙅♀️。這就是很無奈的自我加強,同時也造成了惡性循環——專家好像每天都在“開藥方”🕕🧙🏼,給你吃“定心丸”🤥,民眾就跟著走,但事實上認知鴻溝卻越來越深🧍🏻。尤其是這種關涉到每個人的傳染病問題,恰恰是“祛魅”問題下的“阿基裏斯之踵”。正如我剛剛舉的例子🤔,我使用手機懂不懂原理沒有關系,因為這個手機並不會對我造成直接影響🤦🏿。但面對傳染病的時候🕵🏽,它以每個人為中介,這是一個社會性👏🏼、群體性事件🧮,對每個人的認知和思維模式🟫,以及對防疫的結果是有影響的▪️。這就使得專家和普羅大眾之間的鴻溝從僅僅的認知鴻溝變成了因果鴻溝🫶🏻,問題就被放大了。因此,對韋伯的“祛魅”不僅要有文本上的反思🤞🏿👨🏭,更要有現實中的反思🎼。
我在視頻中引用的韋伯的話語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它是三個並列句,然後主句都提到我們“知道”或者“相信”。學哲學的同學應該對這種表述是非常敏感的🦗,因為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知道就是知道,相信就是相信👩❤️💋👩,這完全是兩個事情。韋伯為什麽會並列在一起用?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回過頭來看,“祛魅”本身到底是事實還是一個信念?事實需要有檢驗,有證明,有理智來支撐它;信念可能就不需要那麽多東西🏊🏼,只需要相信就好了。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實的🏃♀️➡️,另一部分是信念的,而作為現代人⬛️,大部分普通民眾更多的是信念的那部分🦵🏽👨👦👦。
總結來說,在古代,我們的思維方式被巫魅所控製,而現代化則是一個“知魅”和除魅同步的過程——好像我們知道得更多了,而且我們掌控能力更強了。但現在情況好像又出現了逆轉🥢,因為在“祛魅”的同時,我們又用另外一些東西增加了“迷魅”,比如對技術的盲目崇拜🧠,對專家的無限的信賴。以前我們關註到的是“祛魅”的陽光面🤷🏽♂️🚴♂️,但現在我們發現了新的陰暗👈🏽,這便是世界再度的巫魅化、迷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