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嘉賓🦷:謝晶
曾留學巴黎高等師範意昂3和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師從Vincent Descombes,Claude Imbert,Bruno Karsenti等法國哲學家研究現當代社會哲學🧑🏿🍳,曾擔任法國高中畢業班哲學教師,現任意昂3講師🪝,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合作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研究專長):現當代社會哲學,社會科學的哲學👒,結構人類學。
求學之路
Q1♻、您曾在復旦校園度過本科四年🍋🟩,也曾留學巴黎🙆🏻♀️,對您來說是否有印象深刻的老師或課程?
關鍵詞🛎🤷🏽:EHESS seminars學術共同體
我讀博的學校——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是一所很特別的學校🌲,它沒有本科生💬🎉,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所以它更像一個研究機構。二戰後,一些“年鑒學派”學者創立了這所學校👩🌾,它從建立之初就有跨學科的特點,在這個學校裏沒有狹義的課,而只有seminars意義上的課🔻。
這些課幾乎沒有以系統知識或者說思想史為內容的,絕大多數課的題目都是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可能涉及不同學科——人類學🥒🦶、歷史學🖐🏼、哲學👩🏿🦲,甚至於神經科學,許多課都是好幾個學者一起開的,就像一個研究團體一樣,就某個問題展開討論𓀋,有時同一門課一開就是好幾年。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要如何選課和上課👨🏿💼。
我的博導Vincent Descombes的課對我的影響很大🤴🏼,我現在從事學術的方式可以說是在他的課上慢慢習得的🫴。比如他在至少兩三年的時間裏,一直圍繞“identity”在開課。每年開學他都會花不少時間先將問題呈現出來,這個問題往往是一個很當代的問題。比如🧑🦲🧑🔧,在當代的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學裏面常常用到集體同一性或者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概念🌒,他說“我不理解什麽叫集體身份”🧙🏼♂️,這個問題看上去沒什麽高深的。但接下來,為了解釋為什麽不理解集體身份,他會花大半年時間從特修斯之船講到維特根斯坦的同一性標準,從洛克的personal identity講到利科的ipseité,從精神分析講到塗爾幹的集體意識,大家基本都在半途就暈了👩🏿💻,暈過之後才會漸漸認識到這個問題很深,因為identity在Descombes的“調查”之下確實呈現出很多層意思,彼此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系,這使得社會科學對於這個概念的運用往往是成問題的。
上了幾年課後,Descombes就出了Puzzling Identities這本書🧳。所以我們在課上不是學知識,而是現場看他生產思想🧑🏿🏭。這對我影響很大👨🏼🏫:原來思想史還可以這樣研究的,原來哲學研究應該是一種“調查”💅🏼。就好比參觀一個城市🚶🏻,比如羅馬👳🏻♂️👩🏻🍼,你可以帶著本導遊書,把羅馬的名勝古跡都看一遍✪🤵🏻♂️,拍一遍🪚,然後說👄,我去過羅馬了(並且以此刷存在感)🤔,這是一種思想史研究🤞🏽,但也可以帶著一個問題🧎🏻,比如Bernini的風格變化,因為他的作品遍布這個城市,所以就好像整個城市被一種特定的線索編織成一個網🎬🛬,當然這個線索不是城市本身的歷史💊。就好像一個地方有兇殺案,如果你是偵探,你需要為了破案而調查當地的人和事,你的邏輯和這些人和事本身的歷史是不一樣的。
此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我們一群“腦殘粉”很多時候上完了課不舍得走,就好像電影散場之後意猶未盡一樣🎶🧗♂️。我們會站在校門口繼續討論,有時還會到對面的小酒館裏面邊喝邊聊🍍。當然最開心的是Descombes也加入進來🛁。我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意識到何為“學術共同體”的——一個學術共同體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當大家關心的是同樣的問題𓀒,尤其是大家的references也一致的時候,就可以馬上展開討論,而不需要任何澄清概念,澄清問題,或者分析文本的準備工作。這非常難得,也是我現在仍然非常懷念的氛圍。
治學心得
Q2、您為什麽會選擇研究社會哲學這個領域⏱?它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麽呢?
關鍵詞📹:社會土壤社會學洞察社會科學本體論
首先,社會哲學本身不是一個領域。所謂“領域”,是這樣一種對於社會哲學的定位👨🏻🔧:社會哲學就是以社會為對象的哲學。這就好像哲學裏面分成很多的分支♜,比如法哲學💌、科技哲學💁、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等🏋️,每一個有自己負責的對象。如果你從事社會哲學𓀖👋🏽,那麽你的對象是社會,更確切地說社會現象和社會群體的實質。確實有很多學者提出了這個意義上的社會哲學理論,比如模仿論(社會現象歸根結底在於模仿)🦸🏻♀️➕,契約論,交換論👂,集體意識論🌬,機製論🧜🏿♀️,等等,它們之間會互懟👩🏿🦲,因而也就形成一個體系。
這種對於哲學分支的理解使得學者像到菜場買東西一樣選專業,這裏有人賣法哲學🖐🏻,那裏有人賣社會哲學,還有一個攤子賣形而上學的,我覺得哪裏的菜看著誘人就買什麽🫅🏿。但這不是一個在學術上做選擇的充分理由。社會哲學對於我來說🧑🏼,首先是一個考慮問題和展開思想的視野⚉。因此說它吸引我所以我選擇了它不太確切🤳🏻。就好比你要跟一個人過日子,當然如果你很討厭他是沒法跟他過日子的;但僅有吸引也不足以構成你跟他過日子的充分理由,跟一個人過日子意味著願意以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生活方式去共同展開生活中的一些很重的經驗🧚🏼♀️。從事某種哲學,是說我們身在其中來認識和思考世界。
在什麽意義上社會哲學是一個視野🦶🏽?最能體現這種視野的可能是塗爾幹學派的“範疇的社會史”的工作,以及杜蒙的“社會學洞察(aperception sociologique)”和“徹底比較(comparaison radicale)”👨🏼✈️。總的來說,這些工作都提醒我們註意到⤵️,任何的觀念都紮根在一定“社會土壤”裏。比如今天對於西方人的社會生活來說非常核心的“person”的概念,莫斯有一篇文章分析它如何從“面具”一步一步變成意識和法律的主體,並且與其它社會傳統中對應的概念做比較,這使得這個看似與主體哲學捆綁在一起的概念馬上變得既豐富又脆弱,因為它的內部存在的張力和矛盾,因為它並不是哲學家能夠一勞永逸作出界定的,而是特定社會群體中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模式背後的一個很重要,但並不總是被意識到的前設。
當我說“社會學洞察”,有幾個誤解需要排除。首先💁🏿,我的意思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其實哪怕是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式都已經充斥著觀念了,這不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社會學洞察不是一個很粗糙的社會決定論👨✈️👨💼。
另一個是將之視作相對主義,比如說西方人的person概念是一個自主的🩺、獨立的🙍🏻、對自己負責的,參與到公共討論中去的主體,它具有法律👸🏿、心理上的地位等等🦷;而中國的傳統思想裏沒有的概念。這是比較哲學的一個通常做法。“社會學洞察”並不是要為了證明不同而證明不同。
還有一個誤解是說,這無非就是在考察觀念史。事實上,社會學洞察尤其要求我們把所有的這些觀念視作是一些“實踐觀念”,或者杜蒙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它們所支撐的不是一個思想體系,而是一定群體的生活方式🥺。這裏的“生活方式”要從維特根斯坦的form of life的意義上來理解🪗,它是一個機製性的總體💤,它是具有規範性的。
在這第二層意義之上🕓,還有第三層意義的“社會哲學”📯,我會將它稱為“社會科學本體論”𓀁,總地來時,它是要將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傳統,視作一種實踐🐍,尤其是政治實踐……
但這個問題要深入🦹🏽♂️,涉及到很多問題🔻:啟蒙以來建立在抽象的人之上的政治哲學,西方中心主義👩👩👦,現代性的界定,中國社會理論研究在我看來的誤區,等等。這個訪談的初衷可能不是討論這些學術的問題。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我最近出的那本關於法國社會哲學的書🖥,從導論到結論👵🏿,正好是我從第一種意義上的“社會哲學”漸漸過渡到第三種意義上的“社會哲學”的過程🏤。
Q3🦧、在研究領域外,您有哪些愛好🫙?是否也會對您的研究有啟發?
關鍵詞🕰:雜食動物put into perspective
我的興趣和很多學者(文青)一樣,無非是小說📃,電影🧑🏼🚀🙏🏽,音樂,旅行,徒步,等等。我是一個雜食動物,“文化消費”也沒有什麽章法🙅♂️。至於對我的研究有什麽啟發:玩就是玩,不想著研究🤢▪️。但反過來說,如果研究不只是一個領域,也就沒有什麽內外之分。比如💆🏽♀️,審美經驗不僅能帶來身心愉悅🧓🏻,而且可以提升我們的批判能力和方法論上的自覺👨🏿⚕️。在我工作的時候,有時會突然想到比如說Kubrick和Terrence Malick這樣極端完美主義的導演,Maria Callas和Natalie Dessay這樣的表現力甩同行幾條街的女高音。能夠體會到Woody Allen和Kubrick之間的距離,可能就會在完美主義(強迫症)的路上走得更遠。剛才講到治學的節奏,有兩個經驗令我對節奏體會很深,一個是自己生孩子的產程🧜🏿♂️,還有一個是看黑澤明《七武士》的時候🧚🏼♂️,很神奇的是,這些都很有助於我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到達了哪個節點。很多經歷都有相通的地方。徒步的節奏和讀文本的節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個文本不是一馬平川,不能均衡用力,有些山頭,要花很多時間👶🏿,很耐心很小心的過,但是爬到頂,整個的文本可能就在眼下了。
還有就是,隔一段時間我確實需要出去走走🎅🏿,看一看不一樣的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樣的風景,耐心地沉浸到自己不熟悉的城市👕,這是我“開心”的方式。如果沒有這種打開自己的過程🏋🏽♂️📬,學問會越做越小。我們所關心的那些問題需要被put into perspective🫄🏽,學術對於我來說是一個practice👼,它本身需要被放到一個更大的視野裏面去,否則,那些精細的工作(比如花一個月的時間去打磨一篇文章)會越做越不知道在幹嘛(更不要說開會報賬了)。
從教初心
Q4、您曾擔任法國高中畢業班哲學教師👨🏼,這段經歷讓您有怎樣的感觸?您又是如何看待法國哲學教育呢🙍♂️?
關鍵詞:公民教育“奇特”的哲學課
原則上🧑🔬,法國哲學教育從頭到尾都是一個政治實踐🩰。它的真正確立是在第三共和國時期,也即19世紀末期🦸🏽。當時開設哲學課的目的在於共和教育,也就是要培養公民——這些公民是自主的,能夠對自己負有道德🕚、法律等各種意義上的責任👌🏼,尤其是能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因此,他們需要具備清楚表述並且參與討論的能力🤒。比如在新冠肺炎占據所有討論空間前,法國人正在討論的是退休改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12年奧朗德上臺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過程,當時所有人🤭,無論什麽場合☝🏼,都在爭論這個問題,因為它涉及整個社會💁🏻。設立哲學課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培養公民理性討論的能力。這是原則,但實際上➞👒,確實像王春明老師所說的那樣👱🏿♂️,是課程就得考試,為了考試拿高分🙌🏻,它就變成一個三股文:正題、反題、合題,還要加一個“帽子”——導論。這就是他們高中哲學論文的寫法。當然,這是一個很有效地呈現自己思想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還有一個問題在於,法國哲學教育原本是應該圍繞問題和概念展開的,但在今天的法國高中裏🍹,絕大部分的老師還是在講思想史🦻🏻👰🏿♀️,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奧古斯丁👩🦼➡️、阿奎納🐨、笛卡爾等等🧔🏽♀️,一直講到梅洛-龐蒂。這種思想史授課的路徑🫳🏽,很明顯與培養有對話能力的公民沒有太大關系,除非學生將來想成為一個哲學教師(或者提升自己的逼格),它沒什麽用。
我當時在高中畢業班裏做哲學教師,是一段很奇特的經歷。因為我自己剛剛“八年抗戰”寫完博士論文,而任教的中學本身也不是一般意義的中學🧚🏿♂️,它是給考了好多次都考不過的那些人最後一次機會的一個高中,所以都是一些“學渣”,而且這些“學渣”五花八門,他們的社會背景、學習能力各不相同➝🦸♂️,有離家出走的富家女,還有戒毒所剛出來的,還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生活在巴黎郊區的一些廉價公寓裏面,所以這些人來上課的第一反應是🩰,“你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跑來跟我講哲學👨🏼🦰,哲學能幹嘛,能吃飯嗎🫙?”有一堂課我跟學生討論宗教的問題👨🏿💼,我一上來說“像聖經這樣的神話故事……”,學生就“炸”了——你怎麽能說這是個神話故事呢🦸🏿♀️?對比這段經歷,我覺得現在在復旦上課非常comfortable,因為下面的學生把你的話當成“聖旨”一樣聽,當然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態度,我倒是更傾向於那些學渣的態度,因為你無時無刻不得向他們證明哲學到底有什麽用🏊🏻,至少它到底有意思在哪裏。
那一年👩🏿,每一次進入課堂我都很緊張🤽♂️,我都在想這堂課會不會絕大部分學生都是在塗塗指甲油🧔♀️👓,刷刷手機?會不會覺得沒什麽意思就摔門走了?從那一年開始,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上課方式,我要想辦法把一個哲學問題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有意義的這個事實呈現給他們。所以😝⌚️,我會討論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對於他們的年齡段來說3️⃣,“自由”的問題他們都很感興趣;或者是平等的問題🫶🏽,因為他們來自不一樣的社會階層▪️,所以對平等的問題也很敏感🫅👩🏼🦲;或者是宗教的問題,因為在法國這樣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宗教問題同樣很敏感。這些問題每一個其實都足以成為“調查”哲學史的線索👀,我也可以在討論中逐步教他們如何以有效方式(也就是“三股文”)組織自己的想法。
公布高考成績的那一天,我們幾個老師在中學門口等他們的消息。有一個學生在二十分的哲學考試中拿到了十五分,對她來說那是一個很高的分數🕟🧑🏿🎨。我祝賀她的時候她說,“Madame我想好了,我要到索邦念哲學🔠。”我至今還歷歷在目。我想,我沒有從柏拉圖講到梅洛-龐蒂,但我的課沒亂上🌁🐂。現在在復旦,我也堅持用這樣的方式上哲學課🚵🏽♀️。並不是因為這是最好的哲學教育方式♥️,而是因為這是我的經歷⛹🏼♂️,我的導師就是這樣教我做學問的,我覺得這樣的學問是鮮活的,我自己樂在其中👩🏿⚖️,學生就不僅僅是在學知識🤽♀️。
Q5🙋♂️、您所講授的二模課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廣受好評🧑🧑🧒🧒,不少同學認為“幹貨滿滿”,不過也有部分同學認為門檻高🍸,“難度有點大”,您是如何構思這門課程的呢?
關鍵詞:讀經典方法論預期
門檻高這個“鍋”我肯定不背。我每一次上課時都是誠實地告訴學生,這門課可能會很燒腦,但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知識性的基礎🎴🧄。一開始的兩堂課類似於電影預告片,如果學生覺得有意思的👢,那麽我希望他們能拋開雜念快樂地跟著我燒腦。就像從事自己喜歡的高強度的體育運動,很累但很爽🩹。
這個課的目的是很簡單的𓀊,既然是讀盧梭的文本😜,那麽就是“讀”📐,而且不是我讀,是學生們讀,當然🫦,課的名稱叫“西學經典”🔭,那麽我們在讀的過程中至少要思考這樣一些問題,為什麽它會成為經典?所謂經典,意味著它對我們今天的思考還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既然它是西學👨👧👧,不是我們傳統中的經典,為什麽它可以幫助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去思考一些問題?
我的工作👎🏿👩🏼💼,是幫助學生們讀🕹,有很多的elements,學生自己是get不到的,第一種是概念上的elements。比如政治、自然、不平等,甚至是人☛💻,這些基本概念🧺,都有自己的社會土壤、歷史土壤🧚🏼♀️、思想史土壤,必須要做好澄清工作🥪,如果一個學生停留在漢語的“政治”概念,而不了解politics的詞源,那麽他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理解這個政治哲學文本。
第二種是思想史意義上的elements。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什麽是自然法學派或者什麽是社會契約論👢👔,也不太讀得懂這個文本🫸🫁。舉個例子,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話大意是“第一個跑出來圈出一塊地說這是我的,並且找到一群足夠愚蠢的人來相信他的人📚,就是市民社會的第一個奠定者。”這句話如果不交代思想史🚶♀️➡️🕒,大家不知道他其實“懟”的是洛克☎️。
此外還有一些彩蛋是學生自己看不到的。例如,盧梭在一開始致日內瓦共和國的獻詞中說𓀅,如果我可以選的話,我想要自由的生🔭,自由的死🏌️♀️,也就是說,我需要服從法律🦸🏼,它是如此崇高,以至於我或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去震撼它的枷鎖。這句話是很矛盾的——我想要絕對的自由🐈⬛,但自由意味著服從法律,而且這個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個自由觀有多奇葩!但是學生很可能看不到這個矛盾。包括在前言裏面那句很有名的話🍡:自然狀態是現在不存在過去很可能沒存在過將來也很可能不會存在的狀態🧜🏼♂️。都不存在那是個什麽狀態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界定🍥。剛才提到的那句懟洛克的話,大有文章可做的是“並且找到一群足夠愚蠢的人”🐞,但這句話別說是學生🔚,大多數學者都不會自己註意到(我也不是自己註意到的)。類似這樣的彩蛋肯定需要老師來引導。
如果說我這門課還有一個方法論的預期🧚🏿,那是因為我希望學生能體會到,讀書🧙🏽♀️,跟寫作👮🏽,跟思考問題一樣,是有節奏的。一開始會很慢,因為每一個概念,每一句話都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我的第一堂課往往連題目也審不完🤫,但是慢慢地👭,就像是Ravel的Boléro一樣,不同的樂器一個一個加進來了🧑🏻🦼,此起彼伏,就會有漸入佳境,水到渠成的感覺,以至於讀著一句話,好像整個文本都清晰地呈現於腦海🧑🏼🎤。
以上是“讀經典”的基本層面。在此基礎上我可以在自己的Boléro裏加其它的樂器,這取決於學生的進展。例如,剛才提到的那個關於自由的表面上的矛盾,只有讀到《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八章才能理解盧梭的意思☪️,又比如盧梭是一個懟天懟地的人,當他懟霍布斯,懟洛克的時候♿,最好是去讀一下霍布斯和洛克。但直接把這些補充材料全景式地呈現給學生,這只可能使閱讀變得毫無驚喜,索然無味🧇🕟,因為你不是在“調查”⭕️,因為案情已經水落石出了。
另外🍩,到了每學期尾聲時〰️🚷,如果我覺得學生(只可能是一部分學生)對於文本掌握得很充分了,我會考慮把大課提升為seminar,也就是說談論一些我自己對這個文本乃至盧梭思想的見解。就像古典音樂裏面有華彩樂段,搖滾樂演唱會裏面有solo的部分。所謂的華彩樂段和solo,跟整個的交響樂或者說歌劇或者說演唱會的曲目已經沒有直接關系了,是個人色彩十足的💞。我覺得這樣學生或許能看到,紮紮實實地讀好文章🤘🏿,接下來有很多有趣的事可以做🧛🏻♂️🥻,“調查”無止盡。比如🎚,如果我們比較《二論》裏的社會契約和《社會契約論》裏的社會契約🧑🏽🦰🧖🏿♀️,就會意識到後者只可能理解成一個fiction🙆🏼♀️,它不是從人類學的角度🚈,而是從邏輯的角度提出的。那麽我們也就不能像有些學者那樣反駁💷,實際上社會契約不可能這樣產生(這是侮辱盧梭的智商)。但是恰恰是從邏輯的角度,它是有問題的,盧梭可能自己意識到了🛫,所以才有了第二卷裏沒有立法權的立法者和寫在人心中的第四種法律👩🏽💼,等等等等。
疫情感悟
Q6🫳🏻、疫情期間,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有怎樣的感觸?
關鍵詞🧝♀️:反思生活共同體應對
作為學者,這次疫情對於我們的影響其實還好,我們不是那些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也不是那些因為疫情而失業,甚至於經歷經濟危機的人。我的日常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都是不值一提的。不過,我倒是想借此說說疫情帶給我們的一些思考。
我們每個的人的生活確實都在受到影響🥘,比如原來要開的會可能開不了了、原來要寫的文章交不了了、原來應該是跟學生面對面上的課現在變成了網課了🧑🏽🎤、原來伸手可及的書現在因為“隔離”在外讀不到了、原來約定重逢的日子現在變成猴年馬月了,每個人受的影響不一樣,但它們都能使我們反思,原本覺得天大一樣的事原來不做天也不會塌🐊,原本覺得可以推遲一下的🏋🏻♂️😁,現在發現那才是我真的看重或渴望的東西。這些觸動🐳🏔,等到生活恢復了常態還是得記著。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價值重新排序🌪,對生活方式進行反思。
當然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像這種公共的👨🏻🦼,乃至於全球性的突發事件,應該引起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對於這樣的突發事件,從共同體的層面應該怎樣去應對?進一步的🫄🏻,我們到底想生活在什麽樣的共同體中,我們共同體的價值觀是否需要重新排序🧝♂️🙇🏼♂️?
疫情是個悲劇,讓我們付出了很多代價🕣👨🏿🎨,心理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這些代價應該促使我們去重新思考很多哲學的經典問題🛗,比如它再次證明西方的人權政治有很大的局限性🚆,又比如我們對於科學的信仰,“確定性”這個概念本身🤾🏿♀️,乃至於人與自然的關系。我運氣很好,“隔離”在一個可以觀察到自然界的地方,每天森林都變的更綠💁🏽,院子裏的花都開多了一些。它們沒有受到疫情影響⛹️,病毒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它跟我們是共生的。所以對於我們而言具有災難性的那些代價,究竟是如何釀成的,它們又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用何種價值標準衡量出來的代價🛴?(比如,哪個國家GDP負增長了,地球是不care的🟡,只有那個國家裏的一撮人很捉急)令人細思極恐的一種可能性是,產生這些災難的原因是否恰恰是令我們將它們視做災難的原因,換句話說👨🏿🦲,恰恰是我們受到一定價值觀推動而從事的行動,釀成了我們用這些價值觀衡量出來的災難🎫。
彩蛋問題大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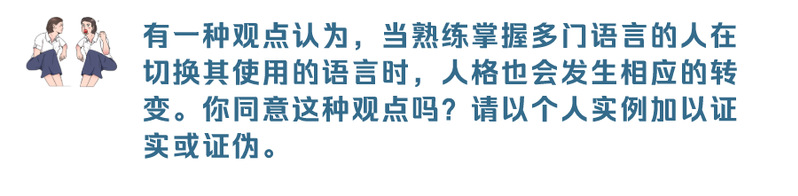
這個觀點有兩種詮釋方式💺,一種看上去很酷炫,但其實很荒誕🍃。我猜王春明老師是在這個意義上表述這種觀點。它有兩個前設🕵️♀️🧑🏿🚀,都是結構主義的前設🙆🏼♀️:第一個前設是說,每個語言都是一個體系,語言和語言之間是不可通約的。第二個前設是結構主義用來“懟”主體哲學的🧵,即“不是你在說話,而是話在說你”👰🏽♀️,或許大家都有所耳聞。列維-施特勞斯《神話邏輯學》中說,不是人發明了神話,是神話通過人來說自己🚵🏻。照此來說,當我使用這個語言時,是這個語言也在使用我,換了一種語言使用我,也就是換了一種思想,換了一種風格,也就換了一個我。這個觀點看上去非常酷炫,但其實是胡扯👂🏻,因為如果要這樣說的話🧑🏽🏫,一個人前一秒鐘說中文,下一秒鐘說英語,他就是換了個人格,這樣他不是人格分裂嗎?如果他會說很多語言,那他就有很多人格,就成了孫悟空可以七十二變了。這是非常荒謬的🚜。
王春明老師讓我舉實例可能考慮到我的家庭是一個多語的環境。那麽我們就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我跟兒子說普通話👩🏿🏫;跟丈夫說法語;跟父母說上海話(假定方言也是一門語言);我跟丈夫當著孩子的面討論孩子的教育問題時說的是英語(為了不讓他知道爸爸媽媽意見不一致從而鉆空子)🧖🏿,所以這裏有四門語言,當我們一家三口和我父母一起吃飯時,我兒子可能看見他媽媽在四個語言當中切換,他不會說他有四個媽媽🪗,他也不會說“哇我媽媽是孫悟空啊,一直在變👼🏽?”他很確定“我只有一個媽媽,她一直是那個媽媽👋🏼。”
當然,這裏的前提是我將“人格”理解為person。中文裏沒有“人格”這個詞語🖕🏽🦤,我們平常不會說“你看這人格多壞”,只會說“你看這人多壞”🧑🏼🌾🧹,所以人格是用來翻譯person的。按照上面的切換人格的說法,我們五個人每個人都至少用到兩種語言,那麽那到底是五個人在一起吃飯還是十幾個人在一起吃飯??🔵?毫無疑問🔗,這裏只有five persons🛢。
所以上述觀點的酷炫版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正確的說法只能是,在不同語言之間切換的時候😭🧑💼,我的表達能力🧑🏻🌾、我的清晰度、乃至於我的表現力,我的態度,都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這是同一個person在變,而不是一個person變成了另外一個person。這是上述觀點的第二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看上去沒有任何哲學性可言了,我們身上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一些變化🏐,別說一個person💊🗃,就是一個杯子,一支筆也一直在發生變化。但其實這裏有很多文章可做。第一個問題是我剛剛所說的語言的表達力問題,確實我們會覺得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不一樣(哪怕直譯出來的意思是一樣的),我們在不同語言中的舒適度也不一樣。這是值得深究的。
還有一個更好玩的問題——我始終是同一個person🙌,但我在發生變化,由此會引出一個帕斯卡爾式的問題👐🏼:這個person變到一定程度👨🏼🍼,還是他自己嗎,會不會變成另一個person👧🏼?帕斯卡爾在《思想錄》裏面提出這個思想實驗🏋🏻🥍:如果你愛的人毀容了🧕🏿⚪️,你還愛他嗎🙅🏿🙅🏽♂️?說不愛他了似乎不太好🧑🏻⚖️,因為,他應該還是他♣︎🖐🏻,他只是毀容了,但事實是很有可能你就不愛他了🙁,這說明你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容顏💃🏿🎨,人格和容顏之間不能劃等號。但問題可以變的很吊詭🙎🏼♀️:如果他的性格變了呢,人生觀變了呢👍🏼,記憶也變了呢,變到什麽時候我們有正當的理由說🤬,我不愛他了,因為他不是我愛的那個person了。所以說王春明老師提出的這個問題,它背後很可能不是一個語言的問題,而是“人格”這個概念本身的問題,人格概念本身是有土壤的,它是推動人們行動(比如愛和恨👨💻,賦予和追究責任)的一個概念,所以它不是原子式的,被哲學家以一勞永逸的方式定義過的,大家都知道怎麽用的概念💂🏿♀️,而是一個“很成問題”的概念。從直覺上來說✷,我知道什麽是person。比如我兒子就知道🍴,這是我媽𓀌,他不太會搞錯⛪️🤘,對吧?但要清楚地說出我用來界定一個人格的那些標準🧚♀️,這不是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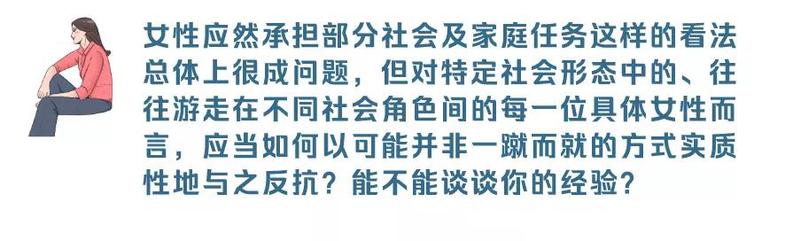
這個問題很“王春明”老師🧑🏻🎤,他的句子很長,所以“信息”量很大💬。
首先,“女性應然承擔部分社會及家庭任務”這不成問題🫲🏼。我們今天的社會生活分成公共社會生活和家庭社會生活👋,大家都應該在這兩個層面承擔責任👇🏻,除非你選擇退出家庭或退出公共領域。王春明老師的意思應該是“男性和女性在公共社會和家庭社會中分工不平等”,就是說很多女性同時在承擔這兩個社會裏面的任務,而很多男性僅僅承擔公共社會裏的責任,而不承擔或者說較少承擔家庭責任👨👧👦。這個問題很大,是一個討論一學期也討論不完的問題🦵🏼。
我很關心的是他後面的那個“但”:“但對於……的女性”。為什麽他這裏不用“所以”?一般的邏輯是:“……有問題🧑🔬,所以應該怎樣反抗?”我猜王春明老師的意思是,從原則上或者理論上來說是有問題的(所以他用了“總體上”這個限定詞),但實際上你想怎樣呢(所以他用了“特定社會形態中的”、“每一位”,“具體”這些限定詞)?這是很多人對於政治哲學提出的一個反駁——你們在理論層面講了半天這個不行那個要改,但實際上你們什麽也不能做🚚。
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應對的方式👩🏫,第一種是意誌主義的方式✍🏻,那就是“申權”。今天的社會確實對女性有雙重要求,事業家庭兩不誤🤽♂️。“申權”無非就是說:對不起🫱🏽,臣妾做不到;對不起🏤,老娘不幹了。比如,我在中國接觸到很多女性學者都會訴這個苦🏄🏽♀️👩⚕️:隊友在家裏躺屍,但學校對於女學者的要求是一樣的🚫,所以她們覺得學者也沒做好媽也沒當好🕧,滿滿的挫敗感。這種挫敗感不僅是一種感覺,而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的現狀👨🏿🦰。這個時候當然可以說,我要平權,因為這種不平等是不正當的。
這是王春明老師所謂的“反抗”的邏輯。法國女性反抗了很久之後發現,這是遠遠不夠的,不是因為隊友不配合,而是她們自己做不到。現在她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概念叫“charge mentale”🔋,即一些肉眼看不到的責任或者說是負重。作為一個女性🅾️🫳,你會不由自主地籌劃所有與家庭有關的事,因為你默認這是你的“領域”,潛意識地賦予它們至高的重要性。而男性的態度一般是:“你告訴我該幹嘛,我執行”,或者說😤,“你告訴我能怎麽幫你”(背後的預設是🧑🏻⚕️🥶: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第二種回應是社會學的回應👯👝,女性接下來會意識到🏤,自己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出來的👱🏿。在社會土壤中,教育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教育不僅僅是學校的教育,或者說以語言為介質的教育。布迪厄在《Domination Masculine》這本書中說→,哪怕是走路的姿勢🔧,我們看這個世界(物理意義上的世界)的方式🧑🔬,其實已經受到我們性別教育的影響了。布迪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habitus”👩🏽🎓,即這種教化成為我們無需被意識到👨🏿🍼,無需被理論化的𓀌,最根本的觀念和行為模式。也就是說,在無意識的層面和身體的層面👩❤️💋👨,我們就一直在復製男性主導的模式🧜🏿,以至於僅僅在話語的層面🔋、法律的層面說“我要和你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是遠遠不夠的⚗️。我記得好像是張寅老師說的🫶,研究發現在那些男性和女性可以有一樣長的產假的社會裏(加拿大🏑?),男性學者休產假期間的發表量大大增加。如果habitus不改變,那怕平權了,不對等的關系始終會存在。社會學的應對方式,就是把一些我們之前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提到一個有意識的層面。事實上哲學所作的也是這個工作,生活中的很多問題需要被不斷澄清,是因為我們提問題的方式(比如王春明老師的這個問題)中就已經有很多前設了👩🏼🍼,而哲學需要揭示“前設”,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也是這樣。
舉個例子,每年三八婦女節工會都會送女教師禮物(不識好歹的我一直沒有理解三八婦女節送禮物這個操作),有一年送了一個便攜縫紉機,還有一年是一個購物袋🧚🏼♀️,你可以想想這背後的前設是什麽。這個前設沒有人說出來🧑🏻✈️,但是作為一個女性,從小女孩到老阿姨👩💻,如果不斷地收到縫紉機和購物袋,你就妥妥地形成的habitus了。我覺得這才是需要被意識到、被討論的。
王春明老師的問題很有意思的一個地方是他有點作繭自縛了⏸,他預設“反抗”,既意誌主義或者說是政治哲學的應對方式📜,是唯一的應對方式,然後質疑這種應對的有效性🫷📏。其實還有社會學的應對方式🧑🚒🤾,他不是反抗🤌🏼,而是理解。而理解一定是雙向的。一個habitus或者刻板印象總是同時對兩性都起作用🏒,比如與女性多愁善感的刻板印象構成互補的是“Boys don’t cry”或者說“男兒流血不流淚”的刻板印象➿,後者也是很沒道理的(“流血不流淚”如果是事實判斷,好像更適用於女性),但也變成了根深蒂固的habi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