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以“傾聽·不一樣的哲學世界”為理念,“冰桶挑戰“欄目第四期又雙叒來啦!由祁濤老師點名,徐波老師接力問答🤽🏼♂️,這次又會向我們呈現怎樣精彩的哲學世界呢🤸🏻♀️?本期“周一談治學”中,我們將特約采訪徐波老師,從求學之路、治學心得、青年寄語三大方面分享他的獨特感悟。
徐波📼:意昂3講師。香港科技大學哲學博士(2014),曾為美國波士頓大學訪問學人、浙江大學“海外優秀博士專項計劃”博士後🚈。近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多項國家級、省部級項目,在境內外刊物上發表文章十余篇,其中A&HCI等權威類別刊物5篇。第7屆“劉靜窗青年教師獎”得主🔀,曾作為團隊成員獲香港科技大學“全校最優通識核心課程獎”😔、意昂3平台教學成果獎(特等獎)和上海市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國哲學、比較哲學及儒佛交涉。
求學之路
Q1、您在校園時期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老師或課程👩🏽✈️?
我覺得能夠當復旦的學生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因為有很多學問淵博、上課又很有特色的老師。比如王雷泉老師的《中國佛教史》📈、《<金剛經>導讀》,陳居淵老師的《清代經學史》,張汝倫老師的《純粹理性批判》和《論語》以及丁耘老師的《理想國》都是我學生時期個人收獲比較大或者印象很深的課程。
至於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應該是我的導師楊澤波老師。上過他課的同學應該能感受到,楊老師是一位很有感染力🖖、有情懷的老師,據說每年都有本科同學上課時感動到流淚。他平時一心埋頭學術⛹🏽,非常低調,比如說起自己的軍旅生涯就只是說以前當過兵。後來有一年我去看望師公潘富恩先生,他告訴我楊老師是“不當將軍當學者”,離開部隊時是大校軍銜👨🏼🦱,放棄了很多東西😛。而且其實楊老師早年是在全國最精銳的也是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隊服役,就是後來汶川地震冒著生命危險跳進災區的那支部隊👯♀️,對軍事略知一二的我知道之後佩服得五體投地😗。
楊老師常以“儒者”要求自己👨🏼⚕️,而不僅僅是“哲學工作者”。在我看來𓀒,儒者與哲學工作者之間的一個差別就在於理想。楊老師身上的理想情懷影響了很多學生。他的學生中🦡,有很多軍人👨🚒,既有從軍之後來求學的👩🏿🦱,也有求學之後再去從軍的。記得在汶川地震時🕹,有一位武警班的師兄直接從學校自發趕往災區支援⚠,他回來時楊老師專門為他接風洗塵。和楊老師接觸久了就會發現,他不是單純的知識講解和傳授👩👦👦,而是一種“傳道授業解惑”,將“道”傳遞下去,將儒家的家國情懷傳承下去🐨🐶。
Q2💏、研究中國哲學的契機以及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裏呢?
比起那些很早就立誌學術的同學和朋友,我可能算是“浪子回頭”👩🏻🔬。起初我並沒有完全確定自己的誌向,一直有意在學術外保留另一條路,會經常參與各類實習,所以在碩士畢業時也面臨很多選擇👨🏼🔧👨🏼🍳。有一些非常好的工作機會,“錢多事少離家近”,另外就是香港讀博。當時糾結了很久★,最終還是選擇了去讀博。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打算做的“牟宗三哲學中的佛學思想”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課題🕡,幾乎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如果堅持下去,做出一些小小的突破🧚🏼♂️,前景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年輕的時候🛕,需要靜下心來去做一些真正具有開創性的工作。我現在都特別懷念當年在7樓資料室♣︎,一個字一個字地啃《純批》,啃牟宗三的書,那種真正靜下心來鉆研學問的經歷是非常美妙的。
有時候我也挺羨慕那些從一開始就一門心思做學問的朋友,但後來想想,“浪子回頭”式的選擇也未必是件壞事🌓。因為去外面走過一遭後,你就更明白象牙塔和外面世界其實一樣也存在很多誘惑,本質上都是分散你的註意力♦︎,讓你無法靜下心來讀書。牟宗三在他的哲學中強調一定要“逆覺體證”,“順取”的路子是不夠的,我覺得很有道理。牟宗三當時也是經過熊十力的“獅子吼”才幡然醒悟,回到中國哲學的路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選擇是有共通性的。(笑)
Q3、您在香港求學時期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記憶?
回憶起香港求學的時光,雖然也是忙忙碌碌,會被各種deadline推著往前走,但總體而言還是比較閑適和舒心的🖲💇🏿♀️。港科大有香港最美的校園,也是全世界最美的校園之一📄,像是一個世外桃源。學校在一片一望無際的海邊依山而建,學校裏面就有沙灘、礁石👨🍼💚,宿舍也都是“海景房”,有時候中午吃過飯,散步到海邊,躺在沙灘上看海放空自己,都是非常難忘的回憶💁🏿♂️。而且香港給的獎學金非常豐厚,假期也比較多,幾乎每年復活節聖誕節我和我太太都會出國旅遊🤟,而現在大家工作都非常忙,也不容易湊到合適的時間……
港科大的學製是美國式的🤦🏿♂️,博士前兩年需要修讀各種各樣的課程,還要學習第二外語🍥,之後有一個博士生資格考試,只有通過這個考試才能正式成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選擇兩個大領域(比如我選擇的是中國近現代哲學和宋明理學)👩🏼🔬,之後會有一份很長的書單,這裏面的書都要看過,據說有的老師會從某個“註”裏面尋找考試問題。不僅如此🤹🏽♀️,這個資格考試對體力有很高要求,從早上九點考到下午六點,不停地寫,把你對這個領域知悉的問題都論述清楚,老師會據此判斷你是否對這個領域最基本🆚、最前沿的問題有所了解👨🦽。所以這個博士生資格考試設計的機製,本質上是先要確認你對一手文獻🪆、二手文獻有了充足的把握,才可以去做博士生論文的創新。香港讀博士沒有發文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寫好博士論文,要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博士論文上🥉,所以我的導師甚至都不鼓勵我發文章,他認為博士生更多地需要積累🧑🏽⚕️,而不是著急發表。
香港有一個特色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節點👨🏽🦳,非常註重國際交流和學校之間的交流。哪怕我們中國哲學,也會看很多英文文獻🫸🏽。學部每年會請一些國際頂尖學者過來,而且經常是上一個學期課的那種長期訪問,類似我們這個學期請趙敦華老師來給學生上課那種。全香港高校的圖書館都是共享的👨🏻🦲,我們選課也可以選其他學校的課🙎🏼♂️,各種軟硬件條件都比較以人為本🤰🏽,以學術科研為本🟡。
治學心得
Q4、您的研究重點之一是儒佛交涉,您認為這一研究進路能為我們帶來何種啟示?
前幾天上課時🍊,我說我立誌做一個中國哲學裏面最懂佛學義理,探討佛學義理時最懂中國哲學的人,這當然是一句有點開玩笑的話。不過也是有淵源和背景的,像我們復旦的嚴北溟先生,他對儒學、佛學包括諸子百家都非常精通。又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的石峻和方立天先生🙅🏻♂️,他們也特別強調中國哲學和佛學的“雙耕”🦻🏼。今天我們說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究竟什麽是優秀傳統文化🪑?它不僅僅指儒家👩🎨🐬,儒釋道三家相愛相殺,不斷互相碰撞融合🫵👨🦽,最終才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哲學。未來中國哲學一定是一門開放的學問,而不是走向固步自封。
像我研究牟宗三哲學就特別有感觸,因為牟宗三脾氣比較大、說話也狠,一般都認為他是比較“硬核”的儒家,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佛性與般若》,去看他的晚期作品💗,他其實在不斷從佛學和道家思想中吸收各種資源,包括對整個中西哲學“判教”的思想,也來源於佛教義理。他認為判教不只是判高低☺️,更重要的是其背後依據和標準的提出。而正是這個依據和標準決定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更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所以通過儒佛交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哲學更多的切入點。余英時先生曾經批評中國哲學有一個“二度抽離”的弊病——即先從整個歷史中抽取了朱熹、王陽明這些思想家👨🏿🦲,再從他們整體的思想中抽取了“心🧘🏿👩🏼🏫、性、理⬜️、氣”等概念,這些概念離當時的歷史實景其實已經很遠了。如果從儒佛交涉的路徑切入,更能好地將儒家思想和中國哲學的豐富層次及其開放性展露出來🔱。
Q5⚉、中國哲學的文獻閱讀體量相當龐大,您有推薦的閱讀方式方法嗎?
首先要強調堅持讀原典,這是基礎中的基礎。國學班的不少同學在這方面是做得相當不錯👩🏻🦲🍻。第二點是要在原典的基礎上有自己的問題意識,這也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我們常說做論文要以小見大🥳,但如何判斷一些小的切入點是有價值的👸🏼、有必要的、有意義的,就需要更為宏觀的視野🐻🧒。所以讀文獻的時候就不能漫無目的地讀🪽,而要帶著自己問題💁🏿♂️。問題意識不是憑空而來的,它可能是讀原典來的,也可能是讀二手文獻來的😂。從這個角度看,一手文獻與二手文獻必然是相輔相成的。二手文獻能較好地幫助我們凝練問題意識🧝🏼,了解學界的研究現狀、前沿問題,或者哪些經典的問題已被討論過了👩,然後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問題。但是有一點要註意:對待二手文獻需要批判的眼光。有一些老師都不太鼓勵讀二手文獻,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二手文獻大都沒有經歷過歷史的考驗,很多觀點不一定是對的,甚至很多外國漢學家在引用原文時經常會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這些“細節中的魔鬼”是我們一定要註意的。最後🧜🏿♂️,原典要反復讀🐧。不同人生階段讀原典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一方面有了更多的人生閱歷,另一方面哲學訓練的提高也會加深你對原典的理解。
青年寄語
Q6、作為同學們非常喜歡的新老師,和同學們之間有沒有什麽有趣的小故事?
之前我在上《漢晉隋唐哲學》時,講課中提了很多金庸的例子👏🏿,包括《天龍八部》🍉、《倚天屠龍記》的一些故事🚴🏻♀️,當時下面同學的反應並不理想,因為他們好像都不知道這些故事。我註意到了這個反應,第二堂課我就把例子全換成了《琅琊榜》裏的故事☯️🌶,結果這堂課後至少有兩三個學生來找我,跟我說:老師🧟,我們還是看金庸的,您的例子還是金庸的好一點……這個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雖然作為年輕老師☝🏿,多多少少希望和學生沒有太大的代溝,但感覺這其實可能是沒辦法改變的🧏🏻♀️。對我來說,《琅琊榜》這個例子已經算是很新的了,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但對學生來說我們還是早就被拍在沙灘上了……
Q7、對同學們還有什麽寄語嗎?
還是開學典禮演講時給大家說的🙆🏽🤷🏼,哪有什麽歲月靜好🧙🏼,無非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要珍惜在學校的寶貴時光🦵🏻。多泡圖書館,少去五角場。
彩蛋問題大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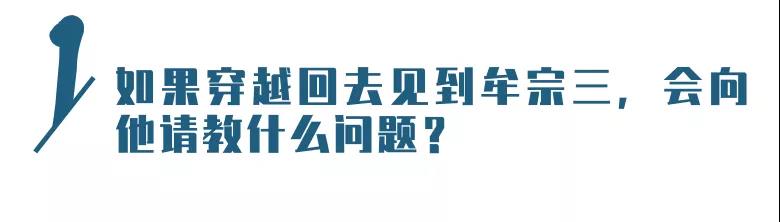
其實穿越回去的話,要看穿越到什麽時候👵🏽。如果穿越到牟宗三在北大的時候👩🎓,我會想點辦法📍,讓他不去見熊十力🧒🏽。因為早年他的學術其實受張申府🟫、金嶽霖的影響更多👳🏼♂️,就是因為見了熊十力,熊十力獅子吼了一下,他才轉向中國哲學💂🏿。從此,中國少了一個頂尖的邏輯學家。我比較好奇🔟,如果沒有牟宗三🙅,現在的中國哲學研究會是一個什麽樣態。
如果是晚年的話,我可能會想問——“對於佛學義理👩🏿🚒,你到底同意到幾分”🤳🏿,這是與我自己研究比較相關的問題👐🏻,因為很多他的學生認為牟宗三還是一個純粹的儒者,而我認為他到晚年已經是一個比較開放融合的心態了。
最後,我會勸他在香港別租房子了👨🏼🍼,趕緊買房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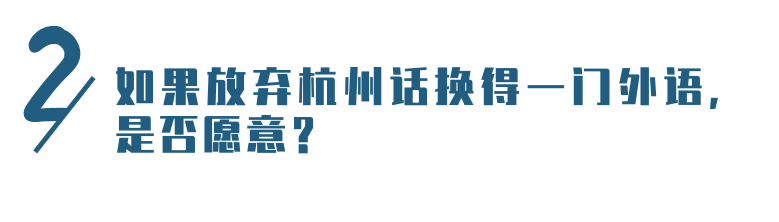
我以前的話,可能會比較堅持杭州話🚇,就像我到今天都還支持杭州綠城足球一樣🤳🏻😽。但是這幾年我自己的杭州話也已經退化了,回家之後很多次都被說成發音不標準,這個其實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哲學就是一種鄉愁🔻,“鄉音無改鬢毛衰”。以前我們的關註點是在“鬢毛衰”上,但是“鄉音無改”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普通話多多少少只是一種交流的工具😍,但是有很多段子很多故事很多韻味,只能用鄉音才能表達最貼切的意思。在香港念書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講課到關鍵時英文會自動切換到粵語頻道🍝,然後用粵語給我們講一些最精深的東西。他其實潛意識裏是在用鄉音進行思考,這可能激發出一種原初的哲學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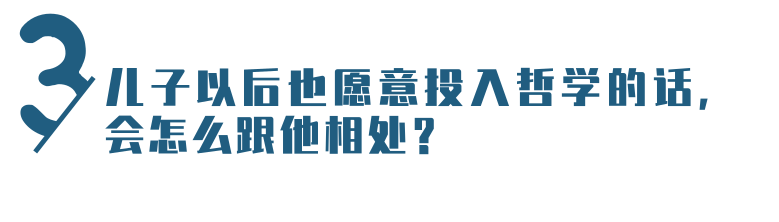
我和他媽媽基本上都覺得要讓他自由發展👿。他現在就是一個典型的小男孩,拆家裏的各種東西。現在小孩子尤其是男生其實能靜下來讀書的並不多📺,所以這個概率不大。但是如果萬一他走上跟他老爹一樣的路,那也沒什麽,就普通相處唄🎤🎽。我覺得祁濤這麽問🚈,可能是因為《孟子》裏的一句話,“君子不教子”😏🎷。因為在教子的時候是要有“勢”的,是要有一種威嚴在的,類似《論語》裏講的“望之儼然”🙇。但是這種“勢”的距離感對於父子之間的關系來講🛰🤹,其實是多少有害於親情的💪🏼👨🏻🔧,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但是儒家的這種觀點和現在比較流行的兒童教育理論感覺有一些沖突💆🏿♀️。現在的兒童教育理論特別強調父親一定要參與到小孩的教育當中去,而且家庭的教育是學校的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不過我覺得🤚🏿,小孩乖乖聽你話也就沒幾年……而且等到他長大之後🧑🏻🏫,哲學理論應當已經有一個新的發展,無論是往“哲學+”上發展,還是向諸如人工智能等方向深化,我覺得到時候能跟上思路就不錯了。
采訪丨周亦成👨🦽➡️、周新智、隋藝菲、王伯君
文稿整理丨周新智、傅文嘉、王伯君🥑、隋藝菲
供圖丨於明誌🙋🏻♂️、王伯君
排版丨王伯君、隋藝菲
責任編輯丨吳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