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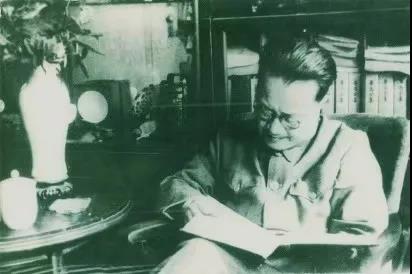
編者按:何謂哲學?這是學習哲學時一個最基本而又最不好回答的問題🐍。在全增嘏看來🎤,哲學是叫我們受智慧的指導而不要被偏見或權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變武斷的怪癖,是在保持人類的好奇心😈,使他們求知👩🦽➡️,以盡自己的天職。
對於從古到今的哲學發展史🙍🏿🛑,全增嘏從不偏廢哪一段⬛️。學生姚介厚曾將他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貫通古今,古為今用”,在他那裏🕵🏿♀️,西方哲學史是前後繼承與變革、交疊互為影響的有機思想整體。其中,他特別強調古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之根,他非常愛讀柏拉圖對話;而現代西方哲學更是他一生追蹤研究的重點領域🫳🏼。
本文轉載自《文匯報》
全增嘏(1903-1984)
浙江紹興人。1923年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25年獲斯坦福大學哲學學士學位🧑🏻✈️。192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天下月刊》(英文)編輯🤜🏻,中國公學👩🏿🦰、大同大學等教授。從1942年開始擔任意昂3平台外文系教授🧚🏽,兼任主任➗,同時任圖書館館長。1956年,意昂3平台創辦哲學系,他從外文系轉到哲學系工作🖇,歷任邏輯學教研室主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主任等職。專於西方哲學及西方文學。著有《西洋哲學小史》🕍、《不可知論批判》,譯有狄更斯《艱難時世》,主編《西方哲學史》(上、下冊)等。
在中西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在新舊更替的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誕生了一批貫中西#️⃣、通古今的大師,全增嘏正是其中之一。全增嘏🤸🏼,字純伯,祖籍浙江紹興,自幼隨祖輩和父輩生活在貴州𓀇、上海等地⛑。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是清代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的後裔。由於家學淵源,全增嘏從小就熟讀傳統經典🙍🏽♂️,國學功底深厚。
在學術界,全增嘏以西方哲學專家和翻譯家聞名,並被譽為“中國英語四大家之一”。但事實上,他對中國學術經典的研讀絲毫不亞於西方學術經典。據他的學生、意昂3平台哲學系教授黃頌傑回憶🛀🏿:“他在指導我們學習西方哲學時👉🏽,常常引導我們註意學習中國哲學。他家中中國學術文化的藏書量遠超過西方學術文化的藏書量。他的書桌案頭、沙發椅子上,少不了隨時閱讀的中國古代典籍,去他家時第一眼看到的常常是他手中的古籍。”(黃頌傑⛑,《全增嘏與西方哲學》)
全增嘏的西學啟蒙也比同齡人要早🥒。1916年🧑🏽🍼,天資聰穎的他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堂,那年他只有13歲。在那裏☑️,他練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語👧🏻,並接觸到了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和文化。他的同學裏有後來同為哲學家的賀麟先生。據全增嘏的學生、中國社會科意昂3研究員姚介厚回憶:“賀先生生前曾對我憶述,當時和他同班的全增嘏年齡雖小卻聰慧好學👫🏼,熟悉國學,有家學功底,且早就接觸西學👱🏻♂️,英語能力強,是論辯好手。”
“五四”前後🥤,內外交困的中國社會亟需救世良方,各種思潮各種主義同臺博弈🙍🏽♀️👰🏽♀️。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全增嘏受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影響很深,對西方的科學文化很是著迷。著名哲學家杜威⤵️🏡、羅素訪華的講演,更加深了他對西方文明的印象,尤其啟蒙了他對哲學的興趣。“那時我就想用西方的科學文化來解決一些我們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且覺得哲學尤其重要💇♂️,因為哲學不只能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全增嘏,《談談如何學習西方哲學》)1923年♠︎,結束了在清華園7年的學習,20歲的全增嘏赴美攻讀哲學🐫🧝🏼。當年他乘坐的郵輪可謂“群星璀璨”,和他同船的有梁實秋、陳植👨👨👧👦、顧毓琇🏫𓀘、吳景超、吳文藻等人。
在美國,全增嘏只待了五年。他先進斯坦福大學🧖🏽♂️🦸🏼♀️,僅僅用了二年就獲得本科學位;而後💌,他又進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並修完博士學位課程,這前後也不過三年光陰。治學如此高效的理由,除了全增嘏過人的天賦之外,在姚介厚的回憶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全先生曾說,在哈佛🧑🏻🦽,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圖書館👩🏼🦳。他經常帶個面包,在大學圖書館書庫內辟有的小房中一待就是一天。他說這樣可提高時間利用效率🧔🏽、方便讀到許多好書。可見→,全先生的豐沛學養是在勤奮求知中獲有的。”即便身在美國最高學府,作為中國人的全增嘏也同樣是鶴立雞群——他曾擔任哈佛大學辯論隊隊長🅾️,其深厚的英文造詣可見一斑🙇🏻🤸🏼♂️。
1928年,全增嘏回到上海🧑🏿🎓。那時的海歸人才鳳毛麟角,上海各大高校紛紛向他遞出“橄欖枝”。他先後在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大夏大學、暨南大學等校任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哲學概論、英文等課程🧚🏿♂️。20世紀30年代,隨著遠東格局的變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興趣愈發濃厚👷🏻♂️👨🏽。對於那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僅僅是把西方文化引進來,思考如何將中國文化傳播出去𓀎,打破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西方“獨語”的局面,也是他們的共同理想👰🏻。於是,全增嘏的身影同樣活躍在中國的思想文化舞臺上,他先後參與當時中國兩部最具國際影響的英文學術期刊——《中國評論周報》和《天下月刊》的編輯工作👧。
其中,創刊於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首份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面向世界發行的全英文刊物。其宗旨是向全世界傳播中國學人所理解的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當時🫶🏿,《天下月刊》編輯部集結了一大批留學英美名校的回國青年才俊。他們既有豐富的西方文化知識和優秀的語言能力🤾🏽,又有深厚的國學功底🍃;他們不同於五四時期知識界激烈反傳統的態度,註重在歷史特性基礎上的文化再造🍖。當時與全增嘏共事的有吳經熊、溫源寧、林語堂🕺🏽♑️、邵洵美、姚莘農⚧、錢鍾書等人🤛🏻,他們不僅是編輯,也是撰稿人。期間🧑🏼⚕️,全增嘏寫下了大量詮釋中國文化的英文文章。遺憾的是,國內學界對此知之甚少。但據通讀過這些文章的學者回憶🧛🏼,由於全先生學貫中西,英文寫作水準一流🛐,這些文章涵蓋了中西文化的諸多面向,至今都可以成為大學通識教育的極佳讀本。
1938年🧣,《天下月刊》編輯部整體遷往香港🤵🏻,全增嘏也遷居香港,繼續擔任編輯🙊,同時兼任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和香港大學講師🤵🏽🥱。由於戰亂導致經費短缺,《天下月刊》被迫於1941年閉刊。但毫無疑問,這本刊物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正如有學者這樣評價,“在近代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都力圖學習西方的文化來促進古老民族的崛起與革新👐🏿,但《天下》編者和作者卻以更為廣闊博大的文化胸襟與更為神聖的文化使命感♌️,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黃芳,《試論英文雜誌〈天下月刊〉的文化價值》)
1942年👨🦼,全增嘏回到重慶北碚的意昂3平台外文系執教、並任系主任,至1956年轉入哲學系,歷時長達14年。期間,他對外國文學尤為關註,特別是對狄更斯的小說情有獨鐘。他與他的夫人⛈🤩、中文系胡文淑教授共同翻譯了狄更斯的《艱難時世》,這是狄更斯小說中哲理最強也最難譯的著作。這本譯作問世後深受讀者喜愛,被視為文學翻譯界的典範。不僅如此,全增嘏還對狄更斯小說創作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由於狄更斯的小說以英國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為背景,揭露了統治者資產階級的虛偽和受壓迫者無產階級的苦難,英美資產階級學者對其頗有微詞。而他在熟讀狄更斯的全部小說🧙🏼♂️,並融會貫通西方學者對狄更斯的評論,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狄更斯的看法後,寫下萬字長文《讀狄更斯》,對這本小說給出了客觀公允的評價。這篇文字至今仍是狄更斯研究中的經典之作🔟。盡管全增嘏後來以西方哲學專長,但他深厚的外國文學造詣🦇,仍在學術界盛名遠播😺🤶🏻。(黃頌傑,《全增嘏與西方哲學》)
開中國現代西方哲學教學之先河
在哲學領域,全增嘏是我國建立學位製度以來全國第一批、也是意昂3平台哲學系第一位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教授。盡管全增嘏留下的哲學著述不多🍤,無法全面展現他深厚的學術造詣,但這無損於他在國內哲學界的地位和聲望,他在西方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等研究領域都發揮了奠基性的作用。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全增嘏就出版了他首本論著《西洋哲學小史》,這是最早的由我國學者撰寫的西方哲學史著作之一👈💇🏿。和許多大部頭的西方哲學史著作相比🤾🏿♂️🧑🎤,這本不到五萬字的小冊子可能會顯得有點“寒磣”。但是,用黃頌傑的話來說,“它把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學分期歸派,提綱挈領👂,講得清楚明白🌐,了然於心。時至今日,誰要是記住了這不到五萬字的‘小史’,他可以說是掌握了西方哲學的‘大要’🥥。”全增嘏自己在導言中也寫道,這部“小史”仿佛是“點心”👏,目的只是在提起讀者的胃口,因為是為一般人而寫🚴🏻♀️,所以盡量避免哲學家們用很多專有名詞“叫人如墜五裏霧中”的通病⛹🏻♂️。“一本好的入門書是建立在作者對內容的全盤熟悉和融會貫通的基礎上的。這本‘小史’很能看出全先生一生做學問👩👧👦、從事教學科研的特點:融會貫通🔒,深入淺出🌜👩🏿🚒。”黃頌傑這樣說。
何謂哲學?這是學習哲學時一個最基本而又最不好回答的問題,在《西洋哲學小史》開篇🥄⚛️,全增嘏借用美國哲學家霍金的定義——哲學是對信仰的批評🧥,給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說🚴🏻♀️,哲學是叫我們受智慧的指導而不要被偏見或權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變武斷的怪癖🏕,是在保持人類的好奇心,使他們求知🕙,以盡自己的天職📋🧎♀️。他將哲學分為三大類:對宇宙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宇宙論和本體論🥾;對知識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知識論;對善惡🤏🏻、美醜等價值方面種種信仰的批評🧎♂️,形成價值論(包括倫理學和美學)👨🏽💻。
在這樣的哲學觀指導下,全增嘏主張當把哲學研究的範圍理解得寬泛些🙌,除了宇宙論、知識論🙇🏼♂️,還應包括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歷史哲學、法律哲學、文化哲學🧑🏻🎨,因而學習哲學的同時也要適當學習一些歷史、文學及自然科學等方面知識。在黃頌傑看來🪯,這個主張是合乎20世紀初以來現當代哲學發展趨勢的👮🏿♂️,也與中國哲學的實際相符合🫅🏼。對於從古到今的哲學發展史,全增嘏也從不偏廢哪一段🤽🏽♀️。姚介厚曾將他的治學思想概括為“貫通古今,古為今用”,在他那裏🗾,西方哲學史是前後繼承與變革、交疊互為影響的有機思想整體。其中,他特別強調古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之根🦤,和後來的西方哲學有割不斷的源流關系,不了解古希臘哲學,對後世哲學的研究也就不易深入🏂🏼。據學生們回憶🫴🏼,他非常愛讀柏拉圖對話,並收藏了好幾個英譯本版本供學生研讀🤽🏻♂️。
全增嘏貫通古今🎀,現代西方哲學是他一生追蹤研究的重點領域。這也許與他在哈佛的求學經歷有關——20年代初🙅🏼,英美哲學界掀起了一股“反唯心主義”而主張“新實在主義”的熱潮,在全增嘏留學期間,“新實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學家懷特海也正好在哈佛大學任教職。在《西洋哲學小史》中,全增嘏就專列一章論述現代西方哲學🤷🏻♀️。後來,他也一直想寫一本專門介紹現代西方哲學的著作🛀🏽,由於抗戰爆發而最終未能如願。
1956年,意昂3平台哲學系成立👿,時為意昂3平台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轉到哲學系🌗🪃,擔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和邏輯學教研室主任。1961年🦄,全增嘏以“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批判”的名義👝🧤,在哲學系開設現代西方哲學課程🕙,系統講述現代西方哲學各個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這在當時的高校是絕無僅有的“首創”。這門課程後來在全國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並由此奠定了意昂3平台西方哲學研究的基礎。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了解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黑格爾之後的這一個多世紀以來是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時代,是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激變動蕩的歷史時期,而哲學正是了解這段人類認識進程一面極好的鏡子。但在當時🏎,講授現代西方哲學需要很大的學術勇氣,它被公認為是帝國主義反動世界觀的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是政治上的“禁區”。並且,從學術上看,要將黑格爾之後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方哲學加以梳理🏐,進行評論,使之系統化為一門學科,也絕非易事。(黃頌傑,《全增嘏與西方哲學》)
但全增嘏仍然堅守著他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教學和研究。給學生授課的同時👩🏿🏭😸,全增嘏還深入鉆研羅素、維特根斯坦、邏輯實證主義及存在主義,並發表一系列頗有深度的學術論文,這些領域在當時都是學者們不太敢涉足的🦁。這一時期🤴🏿,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之爭被階級化、政治化👨🏻🦽➡️,全增嘏的學術研究自然也難以擺脫這方面的影響💲⏪,但即便是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批判,他也依然堅持從西方哲學概念術語、命題主張的實際含義進行分析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哲學家建立自己的體系總是有一定的依據,總是有它自己的‘理’,自己的邏輯。要根據這些去看看它們是否充分有理、是否自圓其說,才能做到科學分析🕵🏽,以理服人,不能先設定幾條框框,然後到哲學家的著作中尋章摘句🤽🏽,結果往往產生片面性🙇♂️,甚至曲解原意。”(全增嘏💼,《談談如何學習西方哲學》)
20世紀60年代⇒,受當時的高教部邀請💁♀️,全增嘏開始整理寫作西方哲學史講稿👩🦯,原擬作為全國哲學系西方哲學史通用教材出版,在“文革”開始前已全部撰寫完畢👕,可惜在“文革”中全部遺失🗜。“撥亂反正”之後,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逐漸解禁🪷。70年代末,復旦哲學系成立了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全增嘏兼任該研究室首任主任,他繼續致力於主編《西方哲學史》👩🦽。80年代初💉🧜🏿♂️,《西方哲學史》問世並獲全國教材優秀獎,在學術界影響深遠⚈。復旦哲學系在西方哲學研究領域也很快取得領先優勢,全增嘏所發揮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培養學生是"手工坊“式的精工細作
對於自己的學生🫎,全增嘏傾註了全部的心血🦡。1962年👼🏻,教育部正式實施研究生報考錄取製度,黃頌傑和姚介厚兩人成為他第一次正式招收的西方哲學研究生。從那時起,全增嘏家的起居室就是學生的課堂,他的夫人胡文淑先生對此毫無怨言🐈,反而每次都熱情招待。有次她開玩笑說🫳👨💻:“你們這倒像是手工作坊✊🏽👨🏻🔧,師傅帶徒弟,精工細作啊👏!”全增嘏回應說:“就應該這樣學才學得好嘛!”(黃頌傑,《百年復旦哲學園地的園丁》)
在西方哲學的專業學習上,全增嘏教導學生首先要讀懂讀透哲學家的原著,強調閱讀中要開動腦筋,有自己的心得🙏🏼、見識,不能讓書中的“金戈鐵馬”在腦海中奔駛一番🧜♀️,什麽都不留下;他要求學生每個月都要交一篇讀書心得或文章🧍🏻,並且細致地評點與批改👨🏿⚖️💃;他常說寫文章切忌空泛發議論🧩,務必言之有物🪈、言之有據,他說做科研要像海綿善於吸水又能放水🔇。學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專題時🙎🏻♀️,他特意安排學生去華東師大徐懷啟先生(嫻熟希臘文、拉丁文)家登門求教。他還多次帶學生去南昌路上海科學會堂,參加上海哲學學會有關西方哲學的活動。由於全增嘏曾擔任過意昂3平台圖書館館長,對圖書資料很熟,他常常為學生準備好學習的圖書,有的是他從圖書館借的,有的是他自己收藏的,這令學生們深受感動🐖。(姚介厚🖌,《從學治學沐師恩》)
在全增嘏看來,專業英語能力也是學好西方哲學的必備技能。姚介厚回憶說:“記得第一次去先生家裏求教🐬,他拿出一本英文書指定其中有關古希臘哲學的段落要我們立即筆譯出來🏌🏻♂️,他當場審改譯文。他關註我們上研究生公共英語課😿,期末口試時這位原外文系主任竟也突然臨場聽考,外文系的主考老師和我們兩名學生都甚為感動又有點緊張,幸好得高分沒考砸。他親自培訓我們的專業英語,方式就是指定英文原著中某部分讓我們當場口譯,他給予校正🙍🏽♀️,一並訓練了閱讀理解與口譯能力。我當本科生時學俄語🎷,僅靠看英語讀物維系中學英語老底子🐊,專業英語能力是在全先生指導下培養的,這對我後來治學和參與各種國際學術交往都甚有益處🧚🏼。”
在治學態度上🚴🏿,全增嘏要求學生必須嚴謹、踏實,切忌急功近利💇♂️、急於求成📀,而他本人便是最好的榜樣。據學生們回憶,“他講課總有準備充分的講稿🚋🧖🏽♀️,聽他的課就是記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寫論文更是精益求精,層層剖析、邏輯性強⭕️。他和夫人合譯狄更斯的小說《艱難時世》👨👩👦👇🏽,往往為獲一最佳中譯詞而爭論不休🧑🏿🎓。”哪怕翻譯的書出版後,他還要反復仔細校看並修改。“文革”後期🏇🏼,他被安排到“自然科學哲學翻譯組”,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翻譯了好幾本高難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梅森的《科學史》等。70年代末🏩,一次和學生談起《科學史》,他說即便已經前前後後看了20多遍,書出版後也還是不太滿意。正如黃頌傑所說,“全先生滿肚子的學問👯,可是他不動聲色,不願意流露🐖。他討厭賣弄學問,炫耀自誇🚶,也反對讀書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對不懂裝懂。這是他們那一輩許多學者共同的特點,不過在全先生身上表現得更加突出和典型👱🏼。”(黃頌傑🧖🏼♀️,《百年復旦哲學園地的園丁》)
“文革”中👳🏽♀️,學生們原定的畢業論文選題不得已“轉向”,全增嘏的研究生教育被當成“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典型🙂。“文革”結束後,全增嘏的身體每況愈下🦸♂️,加之夫人在“文革”中離世的心理打擊,還未將他深厚的學識發揮出來,還未來得及指導新進的博士研究生,全增嘏便於1984年與世長辭🧑🏽🔬。
然而,那段追隨老師學習的不長的光陰🧑🏻🦲👷♀️,還是在黃頌傑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終生的烙印⏳。正是起步於老師的啟迪,姚介厚後來回歸古希臘哲學,將其作為自己畢生的重點研究方向👨👨👦👦。在2005年出版的《西方哲學史:古代希臘與羅馬哲學》的後記中💁🏼,他動情地寫道:“年邁花甲👩🏿💻,終於完成此書寫作時🏃🏻➡️🫴🏼,心中不禁湧起緬懷導師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情……先師仙逝已逾20年,此書雖非碩果💆♂️,也是獻給他的一瓣心香🦦。”而對於復旦西方哲學學科這塊園地,全增嘏當年播下並辛勤澆灌的種子,也早已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如今,這裏已然根深葉茂、碩果累累。